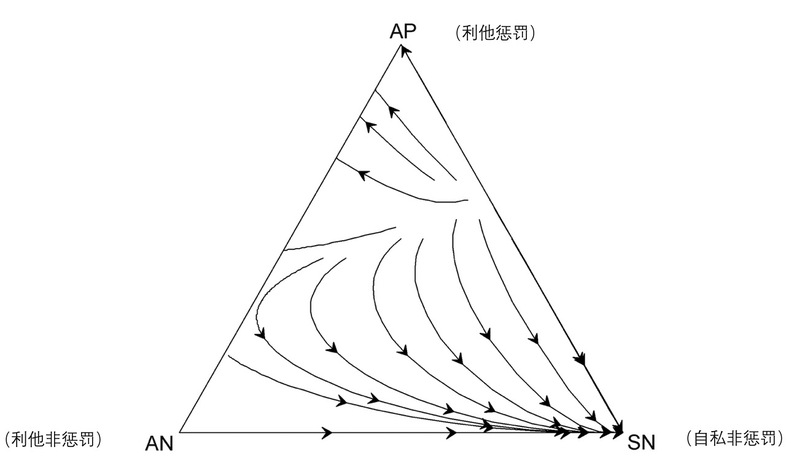
图片来源:Selfishness as second-order altruism(自私作为一种二阶利他主义),2008(5),PANS,https://www.pnas.org/content/105/19/6982
原本是答应小编推一下之前出版的一本译著,推文已经写好,无非是介绍书的内容、学界同仁的积极反馈……云云。今早突然改变主意,既已出版的成果就属于过去,就应该踩在脚下,继续前行。书的质量如何,学术界自有评价,不推也罢。倒是昨日与友人的一段闲聊,促使我想说说翻译这件事。
杨敬年(1908—2016年)享年108岁,193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,40岁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同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。译有雅·科隆诺德《经济核算制原理》(1953年译-45岁)、约瑟夫·熊彼特《经济分析史》(1992年译-84岁)等。7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90岁翻译完成亚当·密斯的《国富论》,百岁时撰写《期颐述怀》一书,回首其百年人生。
回顾杨先生的一生,译著居多,而专著较少,公开发表的论文也不多见。1981年出版第一本发展经济学专著《科学、技术、经济增长》,1988年出版《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》。从1986年(78岁)到2015年(107岁),共发表11篇文章(来自知网检索),其中4篇为书评,有一篇发在《经济研究》上。或许有未公开发表的,不得而知。
还有一人,也是经常会读到的,李平沤(1924-2016年)享年92岁,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,曾翻译卢梭的《爱弥儿》、《社会契约论》、《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、《忏悔录》等经典著作。李先生也极少有自己的作品。或许翻译就是这些前辈们的工作。
但也有一些具有良好的海外教育背景、对英文的掌握犹如母语一般熟稔的学者,一生不出译著。这是这一类学者中最常见的情形。
在早年我国经济社会理论知识相对匮乏的时期,亟待吸收西方的成果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,尤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,各种思潮纷呈迭起,思想界理论界百家争鸣,学者翻译几本著作是有可能确立学术界地位的。
而现如今人们对于译著者的关注度不及以前,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:一是大量经典的经济学外文书籍已经有翻译版,原著本身的分量不足。二是学习者、研究者的英语水平比以往有很大的提高,可以无障碍地阅读原著。中国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,到研究生及以上阶段尽管有时候是哑巴英语,但至少在阅读方面还是过关的。而且有些翻译版可能还存在误导,反而不如自己直接读原版把握得更准确。三是学术评价体系有变化。在学术研究机构的考核评价中,以前译著算工作量,按字数计算,现在一本译著的工作量可能不及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。四是现代化翻译技术的发展。各种翻译软件,小到一页纸、一篇论文,大到一本书,从英文到中文,基本上可以实现所见即可得。尽管很多也是傻瓜翻译,存在语法不对、语句不通、语义不达的问题,但基本的意思可以表达出来。
所以,和几个翻译者聊起,他们的一个感受就是——翻译是个苦力活。
如果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分析翻译这个活,可能的收益:一是翻译一遍比一般性的阅读对文意的理解更深入。很多译著者将翻译作为学习的过程,对翻译中的所得倍感喜悦,同时也积淀了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深度,指待他日厚积薄发。二是满足纯粹的好奇心,也是符合个人的读书写作习惯。有一位友人经常翻译国外的著作,自己是教授经济学的,但对于社会学、历史和哲学都抱有兴趣,边读边写是他的习惯。译著成为他追逐新知的一种副产品。三是满足些许的虚荣心。有人可能还会问有稿费?少得可怜。那版税呢?除非你是大家,否则销量好不好和你没关系。
可能的损失:你把这种比一般性的阅读获得的深意体现在译稿中,并传递给了其他人。你的翻译是更精准的,别人可以在这个肩膀上继续提升,而你这份毫无保留的贡献使自己和别人在一个起跑线上。相反,如果你没有出版,你可能是领先于别人的,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出版专著。其他的损失,当然还包括你写稿投入的时间精力,这部分精力跟自己出版专著所耗费的差不多。
对于一个译者来说,他在读了原著之后,是留着自用,还是整理出版,其中的私心与公理心不好评判,或许也不应该评判。但不管怎样,如果一个人出版译著,对于读者来说,还是应该心存感激的。至少他在更早的时间节点上,愿意分享给读者,与后者在一个起跑线上,促进学术的交流和知识的溢出。



